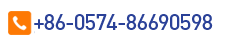

“胖五”成功发射!小小材料撑起大国重器的脊梁 原文链接:https://www.xianjichina.com/special/detail_437754.html 来源:贤集网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发布时间:2019-12-282019年12月27日,实践二十号卫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该卫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抓总研制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公用平台(下简称东五平台)首飞试验星。它将对这型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大型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平台进行全面在轨验证,对提升新技术成熟度、促进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推动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长征五号火箭体内,流淌着零下253摄氏度的液氢和零下183摄氏度的液氧,因此它也被称作“冰箭”。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长五遥三火箭身上,装有该院研制的四型共30台发动机,分别是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2台9吨级膨胀循环发动机,以及18台姿控发动机。
为了让“冰箭”拥有完美的心脏,六院人太难了。

科技日报记者付毅飞 摄
氢氧发动机:冰火两重天的考验
氢氧发动机对于长征五号火箭有怎样的意义?
打个比方,如果把常规火箭和“胖五”相比,携带同样的“行李”,前者自重将达到1000吨,“胖五”却只有600吨。所以,“胖五”虽然看起来胖,身体却更轻盈,运载优势也就更明显。而让它减负增力,液氢液氧推进剂功不可没。
不过,液氢液氧虽然带来了高性能,它们极低的温度也给研制人员带来了不少麻烦,首先就是寻求适合氢氧发动机的制造材料。
一方面,液氢的温度低至零下253度,发动机材料必须经受住如此极寒。另一方面,发动机工作时,燃烧温度在一瞬间就能达到3300摄氏度。这样的工况让发动机材料面临着“冰火两重天”的巨大考验。
在发动机的加工和装配上,也有极高要求。发动机零组件众多,动态组件和静态组件之间需留有一定间隙,这些间隙会随着组件材料的热胀冷缩儿发生变化。发动机在常温状态制造和装配,如果低温时间隙过大,零组件运动时会产生振动;如果间隙调得太小,动态、静态组件抱得太死,又会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要给这些组件设置好精密的“三八线”,需要设计师们好好下一番功夫。
此外,氢易燃易爆,液氧在高压下极易泄漏,一不留神就会起火、爆炸,这都是研制团队需要面对的难题。
液氧煤油发动机:细微之处有看点
别看火箭是个庞然大物,研制装配过程中却要细致入微。例如常规火箭装配时,一根头发丝都被视作多余物,需要清理干净,以免留下安全隐患。
而对于长征五号火箭来说,连装配人员在舱体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是多余物。别以为这是小题大做,如果不及时进行气体置换,二氧化碳会在低温状态下冻结成固态,那就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多余物了。
实际上,在“胖五”身上,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深究。
实践二十号卫星首次搭载多项试验
通信卫星具有通信距离远、覆盖面积大、信道质量高、通信容量大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国际、国内或区域通信,以及海事通信、电视广播等领域。
据五院总工程师、实践二十号卫星总指挥、东五平台总指挥周志成院士介绍,实践二十号卫星重达8吨,是目前我国研制的发射重量最重的卫星,也是目前中国技术含金量最高的卫星。该卫星首要任务是验证东五平台的技术稳定性,由于搭载了十多项国际领先的技术验证载荷,也兼具新技术技术验证的使命。
实践二十号卫星副总设计师裴胜伟介绍,为了更好发挥该卫星的在轨验证效能,瞄准航天未来发展需求,研制团队从全国收集的众多搭载试验项目中,选择了以Q/V频段通信为代表的甚高通量通信载荷、激光通信、深冷回路等十余项国际领先技术试验载荷,其中多项为国际或国内首次。
满足我国未来20年通信卫星需求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卫星公用平台的设计方法。公用卫星平台只需做少量适应性修改,即可装载不同的有效载荷,以此缩短卫星研制周期,节省研制经费,提高卫星可靠性。
实践二十号卫星总设计师李峰比喻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卫星公用平台好比公共汽车,通过搭载不同的乘客(载荷),实现卫星的应用性能。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等为代表的东方红系列卫星公用平台及型谱化产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加速,对我国通信卫星性能跨越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研制东五平台的初衷就是因为我国需要高通量的通信卫星。”周志成说。
按照设计指标,基于东五平台的卫星起飞重量可达8至9吨,载荷承载能力可达1.5至1.8吨;整星功率超过28千瓦,提供载荷功率达18千瓦;载荷舱的散热能力达9千瓦;卫星设计寿命长达16年。
这意味着,相比东三、东四等现役卫星平台,东五平台更大、更强,具有“高承载、高功率、高散热、高控制精度”特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东五平台的出现将填补东方红系列大型卫星平台型谱的空白,可满足我国未来20年高通量通信卫星的需求。
引进不进来,我们就自己造!
今年十一长假,相信很多人因一部电影热泪盈眶,它就是《我和我的祖国》。
《前夜》作为第一枪,率先上膛,便击中了无数人的泪点。
几度停电,阻尼球生锈,国旗掉落在地……一个简单的电动升旗装置居然成为了难题。
夸张吗?可这就是新中国的电力行业,满目疮痍,筚路蓝缕。
1947年的中国发电机最高年产量,只能勉强满足几个村的电力供应。
而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既有人口密集、空间拥挤地城镇地区,又有广漠无垠、人烟稀少之处,也有高山、江河大跨越地形和重冰覆盖区。如何降低空载损耗提高电网运行效率成为电力行业一直头疼的问题。
1975年,钢铁研究总院原精密合金室主任柯成老先生从国外带回来一段不足5毫米宽,1米长的非晶带材,那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种新型材料。
这些只有几十微米厚的非晶带材可用在配电变压器上,其铁损率是传统硅钢材料的五分之一,其代替传统硅钢做配电变压器可节能60—70%,是当之无愧的节能材料。其推广应用将成为我国电网系统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从非晶合金诞生后的半个世纪里,生产非晶合金的核心技术只有几个国家,少数的企业掌握,对中国是全面封锁的。
1989年,全世界投入使用的约100万台的非晶变压器,所用的非晶材料全部来自美国。然而对新型节能环保材料迫切需要的中国,掌握非晶合金的开发生产技术迫在眉睫。
“七五”期间当时三委三部跟美国企业在接触,想把这个技术引到中国,谈了两年,还是没有同意。后来国外一家企业“趁虚而入”,收购了整个美国联信属下的从研究到生产到全球的投资布局。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非晶产业链中的生产设备、非晶带材、非晶铁心一度被国外企业垄断着。
“引进不进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上。”
1981年,国家“六五计划”刚刚开始。钢铁研究总院的原第二研究室承担了非晶研究课题。
△ 钢铁研究总院原精密合金室主任柯成老先生
在拍摄时,这位百岁老人已经记不清你上一句跟他说了什么 ,但他依稀记得自己当年奋斗过的“非晶小楼”。
△ 钢铁研究院原极冷技术中心副主任马鸿良
“那阵就是穷干,没有钱……”。满头银发的钢铁研究院原极冷技术中心副主任马鸿良,腿脚已经不那么利索,但回忆起当年的非晶生产攻坚战,依然神采奕奕。
这群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带领科研团队最先采用石墨材质喷嘴,成功喷制出了200毫米宽非晶带材。
在那些更迭动荡的岁月里,在那座普通的非晶小楼中,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无悔的挥洒着青春与汗水,填补了当时的技术空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伟大突破。
继往开来,进入新世纪,非晶的发展也乘上了时代发展的快车,百吨级千吨级万吨级生产线逐步落成。一批优秀的非晶制造企业涌现出来。
当年参与“六五”、“七五”攻关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如今已经或是步履蹒跚,或是记忆衰退,或是斯人已去。我们试图通过影视资料去讲述一代非晶人的汗水与光荣。
文章来源: 科技日报,新材料在线